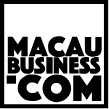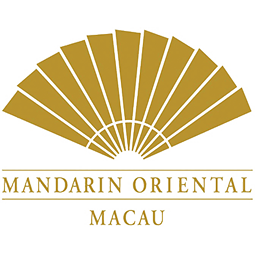文:Inês Almeida
儘管人類免疫缺陷病毒(HIV)80年代便被發現,至今仍被錯誤理解。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禁忌,一個被詛咒的詞彙,是致命性的、骯髒的。許多人都不敢大聲說出來,幾乎沒有人談及。那些被這種疾病困擾的人,每天都生活在恥辱中。
在澳門戒毒康復協會(ARTM)的重返社會支援部門,我們看到了駝背的阿偉安靜、腼腆地坐著。他十分瘦弱,話語很輕柔。我們與他握手,這讓他感到意外。他微笑著,伸出手來。
阿偉於六年前被確診感染愛滋,當時他才50歲。“當聽到消息時,我馬上暈倒了。”他說,“我很傷心,我真的無法告訴你,我是如何感染的。我記得有一次,我幫助一個摔倒在街上,臉上流血的人。我還記得,自己在三角花園洗手間裡,從地板上拿起一些舊針頭,由於我未有小心地處理,這些針頭刺傷了自己。”
他忘記了自己是如何感染的,並承認:“我完全不知道整個過程。”在被確診之前,“我不知道這種疾病是如何傳播的。我記得,當時的澳門周圍都可以看到相關的海報,但我真的沒有去關注。我沒有獲取適當的資訊。”
疾病的確診幾乎是偶然的。“六年前,ARTM宣布了一項計劃,每隔三個月推廣一次愛滋病檢測項目,所有參加檢測的人都可以獲得一份禮物。我無事可做,通過電視節目得知這個消息後,我為了那份禮物而去做了測試。我只想要禮物,聽到自己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時候,我十分很驚訝。”
目前,阿偉的病例由仁伯爵綜合醫院的醫生跟進。他每兩個月進行一次諮詢和血液分析。由於他持有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證,醫院還為他提供免費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。
沒有人知道他是愛滋病病毒攜帶者。連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都不知道。他擔心這會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影響。因為這個名字本身 – 愛滋病病毒 – 具有非常負面的潛在意思。
“我是唯一一個知情人,我沒有告訴任何人,恐怕這可能會影響我與家人的關係。我擔心自己的兒女或許會告訴他們的同學,並疏遠我。我擔心他們會拒絕我的出現。”
阿偉說,愛滋病是一種“著名的疾病”,由於當中最惡劣的理由。“它不像乙肝、肺結核、高血壓、心臟病或其他疾病。承認自己感染了愛滋病病毒並非什麼好事,這種病的名字本身就非常非常糟糕。我很害怕告訴家人我的情況。”
阿偉已婚,卻在一個月前分居。“我從未告訴過妻子,她不知道。即使在診斷之前,我們之間的是安全性行為,所以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她。我們有了孩子之後,我們便開始使用安全套。”
他的孩子永遠不會知道他是病毒攜帶者。“除非絕對必要,否則我絕不會告訴妻子和孩子。如果他們知道我的身體攜帶愛滋病病毒,他們可能會告訴其他人。由於我們最近分居,我害怕別人會認為愛滋病病毒是促使我們分開的原因,但事實並非如此。家裡沒有人知道。沒有人;只有這個中心的人員知道。每個愛滋病病毒攜帶者都希望保密自己的資料。”
孤獨是其中一個最大的恐懼。患者擔心談論病情會趕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,因為缺乏了解。
“如果人們知道愛滋病病毒的真正情況,他們就不會害怕,但人是無知的,他們會避開病毒攜帶者。如果我告訴人們,他們可能會從我身邊逃跑……想像一下,我們都出去吃晚飯,如果他們知道我感染了愛滋病病毒,他們會害怕和我同枱食飯。如果人們能夠多點了解,情況會更好。”
自我孤立
如今,從很多人的態度可以看出,這座城市缺乏信息和知識。儘管害怕孤獨,但患者都會出現自我孤立的現象。對於阿偉而言,這是唯一的選擇。
“我害怕接近人們,害怕開展一切性質的感情。我寧願遠離人們,也不願意與他們交往,因為害怕他們了解我的情況後,會使我的生活處於恐懼之中。最好保持距離,一開始就保持距離。自被確診以來,這成為我生活中的重大變化。”
“在病發前,我在一個協會中有很多朋友,但確診後,我決定離開。我的朋友似乎沒有注意到。有時候,他們打電話給我,問候我。我們聊天,但就是這樣。如果我沒有感染這種疾病,我會與他們更加接近,而不是那麼遙遠。”
恐懼是一成不變的:如果有人發現並告訴其他人,該怎麼辦?然後,就只能選擇孤獨了。 “我留意到,朋友對這種疾病所知不多,所以我寧願不告訴他們。”
有機會與其他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討論這種疾病時,阿偉肯定:他們的病例與他的病例相同。他們都希望隱瞞自己的病情,擔心最終會獨自一人。這令到推廣疾病相關知識變得非常重要。當阿偉談到推廣的迫切性時,他的聲音變得響亮了。
“我感染了,我覺得自己不應該得病。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,澳門不存在愛滋病病毒,我埋怨政府未有保護居民,也未有盡力推廣有關愛滋病的知識。我認為,對於那些年幼的孩子和老年人來說,提供更好的資料會更好。這是一種可怕的疾病,但如果每個人都有相關的知識了,那就不會那麼糟糕了。”
這十三年裡,小王已經學會了如何與疾病共同生活。現時63歲的小王臉上長著一道道深深的皺紋,有些從他的眼睛一直延伸至臉頰,而且他的牙齒早掉光了。
“當我從中國內地抵達澳門時,因吸毒而被捕,並被送到路環監獄。我在那裡接受了體檢,發現自己感染了愛滋病病毒。”
面對診斷的資料,他拒絕接受事實。 “我一開始並不相信,這來得如此突然,我感到震驚。在內地,我使用毒品和共用針頭。我清楚不應該這樣做,而且我通常會拒絕共用針頭,但有一天,向我販毒的人給了我一支注射器。這支注射器被密封袋包好,所以我想,這很乾淨,但它或許不乾淨。”他感嘆道。
小王甚少接觸自己的妻子、兒女和母親,他們都不知道小王的病情。
我甚少回家,他們亦從不與我聯繫,所以我們從不見面。我十幾歲的時候便已離開了父母的家,我很少和家人聯繫。”他說。他的眼睛盯著自己的膝蓋,背部向後彎。
“我不想讓他們擔心,所以我沒有告訴他們。 我也沒有告訴身邊的朋友或其他人。如果有人知道了,他們會認為我會感染他們,因為他們對愛滋病病毒沒有適當的知識。”
必要時,他每年到公立醫院接受兩次檢查和治療。 “一開始,我每年去三次,但醫生告訴我,病情已經穩定下來了,所以我開始每年進行兩次檢查和治療”。
由於背部受傷嚴重,他已經沒有工作很長時間了,而且,剛開始的時候,真的很難接受自己感染了愛滋病毒。
“我與人疏遠,這極大地影響了我的日常生活。現在,我接受了現實,只能面對。”
由於他從未把自己 的病情告訴任何人,所以他與朋友保持聯繫,但小王不確定,當中是否有人知道他的病情。“當我在監獄的時候,那裡有一個專門為感染愛滋病毒的囚犯而設的特殊分部,那裡的人都清楚我們被感染了。”
《澳門論壇報》曾試圖聯絡監獄有關部門徵求意見,但未獲成功。
破碎的夢
阿祖32歲時被確診患上愛滋。當時,他從社會工作局獲得經濟援助,換取藥物,而亦因此他必須每年接受血液檢查。有一天,結果出來了,帶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。現時47歲的阿祖依然記得當時的感受。
“我很年輕,我非常難過。我知道自己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法生育孩子。我一直想成為一名父親。我現在已經不再這樣想了,但這對於當時的我而言,很重要。所以,當我得知結果時,我吃了藥,我想死,悲傷控制了我,我感到絕望,因為我還這麼年輕,卻患上了這種疾病。我當時還吸食毒品,我的家人不想與我有任何聯繫。”
他承認,15年前忽視了共用針頭能夠使其處於感染高風險的事實。他說:“我不知道愛滋病病毒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傳播。我對愛滋病一無所知。我以為,感染愛滋病病毒就像贏六合彩一樣,很難發生,只會在其他人身上看到。”
他與親人間的關係非常複雜。只有其中一個姐妹與他親近,但是這種關係與診斷有關。
“我有兩個姐妹和一個兄弟。我與母親住在一起。有時候,我去看望自己的姐姐,但我從來沒有看到其他兩人。 他們(他的妹妹和兄弟)甚至在我患病前就已經離開了。在那之前,我的家庭已經存在問題。他們認為,父親總把我當作國王對待,因為當我問父親要錢時,他總是滿足我,我的妹妹和兄弟都不喜歡這樣。我的父親非常愛我,不喜歡他們。這已經很長時間了。”
阿祖的父親15年前去世,從未知道自己兒子的病情。然而,家裡的其他人卻很清楚。
“我的母親接受了事實。她80歲,她需要我。我的姐姐對愛滋病病毒一無所知。我試著告訴她,但她總是因為這個病而害怕我。”
並非阿祖選擇坦白,他解釋:“兩、三年前,我的腿部受到了很嚴重的傷害,必須留院治療,家人直到那時才了解到我的病情。醫治我的醫生告訴了我的家人。否則,他們永遠一無所知。”
醫生的決定讓他非常不高興,因為他並不希望自己的家人知道他是病毒攜帶者。他相信,醫生不會說任何話,因此,他沒有明確告訴醫生不要與他人分享這些信息。
“我想到這屬私人資料,所以醫生甚至不會考慮告訴我的家人。從醫院出院後,我的姐姐問我,是否知道這種疾病。我沒有任何回答。我告訴她,如果真的感染了愛滋病病毒,我會非常小心。後來,我承認自己已經知道。”
姐姐無法面對阿祖的病。當阿祖回憶起相聚的短暫時光,他的眼中充滿了悲傷。
“在新年和其他場合,我們會相聚片刻,但就是這樣。我和姐姐一起吃午餐或晚餐,但她因為害怕分享食物會感染疾病,所以將我的碗碟和筷子分開。這讓我很傷心。看到姐姐這樣做,我非常痛苦,因為我清楚病毒不是以這種方式傳播。我試圖向她解釋,但她不明白……她甚至不想說話,以為我的唾液可能會感染她,她和我在一起時戴著口罩。”
他的朋友都不知道。“我甚至沒有告訴那些曾經服食毒品的人,只告訴了那些幫助我進行美沙酮治療的人,我還沒有向以前毒品圈子以外的朋友提及。無論如何,只有幾個朋友仍然吸毒,我不認為有必要告訴他們。我擔心,他們也不會把我當作朋友,我會變成一個人。”
害怕傳染
自從被確診感染愛滋病病毒以來,阿祖一直沒有工作。他說:“我在確診之前是送貨的,但是因為那份工作很可能受到傷害和出血,我害怕會令身邊的同事感染病毒。我害怕在日常生活中受傷,並感染那些可能幫助我的人。如果發生這種情況,如果我們都有開放性傷口,我就可以傳播病毒。”
因此,他的生活盡可能孤立。每隔六個月他都會去仁伯爵綜合醫院進行常規測試和治療。每個月,他都會收到抗逆轉錄病毒藥物。
儘管在如此年輕的年紀便被確診,阿祖仍然曾經結婚,但確診後便與妻子分開了。“在診斷之後,我和妻子分開了,因為我不想感染她。我選擇離開她,但我從未告訴她原因。”
今天,面對種疾病變得更加艱難,但阿祖不再考慮自殺。“我有這種病,我希望我沒有。起初,我想過要結束自己的生命,因為這樣才能擺脫人們對我的想法。多年來,我對自己的生活從來沒有期盼。”現在,他說,他只是不去想。
澳門論壇日報/商訊聯合報道